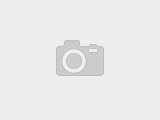北京律师张某被控敲诈勒索案辩护词
案情简介:
2010年5月2日晚22时30分左右,肇事人邹某醉酒驾车,故意撞击张律师的朋友蔡某驾驶的车辆,给蔡某造成人身、财产损害,陆陆续续花去修车费、医疗费等近万元。张律师出于朋友帮忙,代表蔡某与对方协商,要求对方赔偿10万元,否则就向公安司法机关控告,追究邹某故意损坏他人财物的刑事责任。肇事人邹某及其亲属提出私了,经双方多次见面协商,最终同意赔偿8万元。2010年5月25日,根据约定,张律师和朋友蔡某一起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一咖啡厅,接受了对方给付的5万元和3万元欠条。殊料,对方报警,公安民警将张律师及其朋友蔡某当场抓获,5万元被追缴扣押。
2011年9月21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蔡二人犯敲诈勒索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指控称:被告人蔡某伙同被告人张某于2010年5月25日21时许,在北京市西城区枣林前街一咖啡厅内,以将向公安机关告发并追究被害人的丈夫邹某的刑事责任相威胁,敲诈被害人桂某人民币5万元,后被查获。”并认为:“被告人蔡某、张某无视国法,敲诈勒索他人钱财,数额巨大,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及第二百七十四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011年10月11日,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毛立新律师出庭,为张律师作无罪辩护,控、辩双方争论激烈。主要争议焦点有二:
一是张、蔡二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控方认为,张、蔡二人索赔10万元,明显超出了其实际物质损失,于法无据,因此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辩方则认为,蔡某的人身、财产确实遭受邹某的不法侵害,依法享有索赔权,包括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索赔10万元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最终赔偿数额是双方协商而定的,因此,被告人是合法索赔,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二是张、蔡二人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威胁或要挟”。控方认为,两被告人声称“要追究邹某刑事责任”,并以此迫使对方多赔偿,就是“威胁和要挟”。辩方则认为,“要追究邹某刑事责任”是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控告权,也是被告人“维权”的手段,不具有非法性和强制性,不应属于敲诈勒索意义上“威胁或要挟”。 另外,根据相关法律和政策,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不仅可以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和解,还可以就“是否追究对方刑事责任”达成一致。因此,被告人承诺“不再追究邹某刑事责任”,也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2011年12月20日,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申请撤回起诉,西城区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诉后,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张、蔡二人作不起诉处理。
北京律师张某被控敲诈勒索案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的委托,指派我出庭为张某辩护。辩护人经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以及刚才的庭审质证,对案情有了全面了解。归纳全案情况,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其权利遭受侵犯后而进行的维权行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敲诈勒索意义上的“威胁或要挟”,因而,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要挟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在犯罪构成要件上,被告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客观上必须实施了“以威胁或要挟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的行为。但从本案情况看,显然不具备上述要件,具体如下:
(一)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作为侵犯财产罪的一种,敲诈勒索罪也要求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且必须是直接故意。但在本案中,被告人蔡某、张某向邹某、桂某索赔,是一种行使民事赔偿请求权的合法行为,根本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1、被告人蔡某、张某向邹某、桂某索赔,是基于邹某“故意撞车”这一先行行为,具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是行使其合法权利,并非“敲诈”
起诉书指控两被告人于“2010年5月25日21时许”,“以将向公安机关告发并追究被害人的丈夫邹某的刑事责任相威胁,敲诈被害人桂某人民5万元”。根据该指控,似乎本案犯罪事实仅发生在“5月25日晚21时许”。但实际并非如此,此案的“前因”是2010年5月2晚发生的邹某“故意撞车”事件,此后至5月25日,双方曾有过多次电话沟通和4次见面协商。即使是5月25日晚的这次会面,在见面前,双方也曾进行过多次电话沟通,并已就“赔偿8万元”达成了一致意见,然后才约定于5月25日晚见面签署协议。
因此,本案是一个有“前因”的特殊案件,案件的发生、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过程。只有完整地审视全部案件事实,才能正确判断本案性质,而不应裁切事实、歪曲事实真相。本案中,两被告人之所以向邹某、桂某索取赔偿,是因为邹某在2010年5月2日晚有一个“故意撞车”的先行行为。从庭审查明的情况看:2010年5月2日晚22时30分左右,邹某醉酒驾车,故意撞击蔡某驾驶的车辆,并给蔡某造成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这就是两被告人向被害人索赔的事实根据。这一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并无任何虚构成分。基于该事实,在双方之间,形成两个法律关系:一是邹某已涉嫌刑事犯罪,其“故意撞车”行为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故意伤害(未遂)”等罪名,作为被害人的蔡某有权进行控告,包括向公安机关告发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另一个是基于邹某的侵权行为,形成一个明显的债权债务关系,蔡某有权要求邹某赔偿因其行为而给他造成的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因此,无论是蔡某要告发邹某刑事犯罪,还是向邹某、桂某索取赔偿,都是其行使合法权利的体现,如何谈得上“非法占有他人财物”?!
仅就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而言,邹某2010年5月2日晚的“故意撞车”行为,的确给蔡某造成了人身、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第117条第2、3款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因此,基于邹某的侵权行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产生了一个明确的债权债务关系:蔡某依法享有了对邹某的民事赔偿请求权,邹某有义务赔偿因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
总之,被告人向邹某、桂某索赔,具有明确的事实和法律根据,是行使其合法权利的体现,并非虚构事实进行“敲诈”,也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2、被告人向邹某、桂某索赔10万元,同样也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并非漫天要价
在双方就民事赔偿进行协商的过程中,蔡某向邹某、桂某索赔10万元,并最终以8万元达成协议。需要注意的是,在双方协商过程中,直至2011年5月25日双方签署《协议书》时,蔡某的治疗尚未结束,其车辆尚未维修,停车费也未支付,各项损失尚在待定之中。那时候,谁也无法确定蔡某最终会有多少实际损失,因此,不能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要求蔡某一开始就根据其实际损失来索赔。而且,这10万元、8万元的索赔金额,固然超出了蔡某所遭受的实际物质损失(包括汽车修理费为6100元,停车费为1150元,医药费为890元等),但必须指出:这3项物质损失并非蔡某所遭受各项损失的全部,另外还有误工费、交通费等没有计入。除此之外,作为人身权、财产权遭受侵害的一方,蔡某还有权主张“车辆价值减损费”、“精神损害赔偿”等。
虽然“车辆价值减损费”、“精神损害赔偿”两项,在立法及司法层面,未必一定能够得到支持。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蔡某有提出该主张、要求对方进行赔偿的权利。而且,从司法实践看,也有法院支持赔偿“车辆价值减损费”的案例。至于精神损害赔偿,虽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但根据其第1条“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害人仍然享有提起诉讼、提出索赔主张的权利,人民法院也应当受理。也就是说,不能以立法及司法上是否会实际支持,来判断被害人索赔主张的合法性、正当性;即使立法及司法上不予支持,受害人仍然享有索赔的主张权。
从本案情况看,蔡某提出较高的索赔要求,包括精神损害赔偿,也是事出有因,有合理的事实根据和心理因素。在2010年5月2日晚撞车发生时,蔡某深夜正常驾车从车库驶出,遇到醉酒驾车的邹某,无端遭到其手持“改锥”相威胁和故意开车顶撞,不仅人身、财产遭受损害,而且精神上也遭受了很大痛苦。当时,蔡某的母亲正身患癌症住院治疗(随后于2010年6月去世),蔡某每天都要去看护。在其母亲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蔡的最大心愿是满足其母亲的所有愿望,以尽孝心,母亲想吃什么,蔡马上去买,母亲想去哪,蔡马上带其去。恰在这种时刻,蔡某的车因被邹某撞坏,停在交通队的停车场用不上,蔡某无车可用,不仅多花了很多打车费,而且耽误了很多事情,造成其对母亲的终身愧疚和遗憾。因此,蔡某在实际物质损失之外,多提出一些赔偿金额,以弥补其精神损害赔偿,完全具有正当性、合理性。
如此,考虑到“精神损害赔偿”等项目,蔡某向邹某索赔10万元,并最终达成协议赔偿8万元,显然具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并非漫天要价,更不是恶意敲诈。
3、不管现行立法和司法是否支持10万元的索赔请求,蔡某都依法享有提出该主张的权利,不能以索赔数额的大小,来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作为人身、财产权被侵害的一方,根据自己所遭受的各种损害情况,提出相应的赔偿数额,这是当事人行使其赔偿请求权、主张权的体现。至于立法或司法层面,是否会实际支持该索赔请求,这是不同层面的另外一个问题。如前所述,无论现行立法及司法是否实际支持,作为权利受侵害的一方,都有提出索赔主张的权利。对于具体赔偿金额,双方完全可以自行协商,也可以通过诉讼、仲裁等途径解决。根据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则,无论权利受侵害一方提出多少赔偿数额,只要对方自愿接受,就不违反任何法律规定。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共同选择了自行协商、“私了”的解决方式。既然是协商,就会有一个反复交涉、讨价还价的过程。在双方协商交涉的过程中,一方提出要求,对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或者通过讨价还价、压低金额后再接受,这也是对方当事人享有的合法权利。不能因为现行立法和司法不支持10万元的索赔要求,就认为权利受侵害的蔡某提出10万元索赔请求,就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同理,不能说索赔金额超出了立法和司法实际支持的范围,就属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如果这样认定,则实践中出现的大量索赔金额高于法定标准或者高于法院认定金额的维权案例,都可以被扣上“敲诈勒索”的帽子,都可以因而被刑事责任,这岂不荒唐!?
因此,无论在民事诉讼中,还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权利受到侵害的一方提出较高数额的索赔请求,完全是其行使合法权利的体现。不能因为其索赔数额高于实际损失,或者说最终没有得到人民法院支持,就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特别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经司法机关调解或当事人自行和解,往往给予被害人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以取得被害人谅解、并获得司法机关从宽处理。例如,在杭州“胡斌飙车案”中,被告人给予被害人家属113万元的高额赔偿,远远超出现行立法和司法所支持的数额。在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下发的《关于印发对依法可不判处死刑案件全力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典型案例的通知》(法[2009]191号)中,列举了14起经最高人民法院或原审人民法院调解,给予被害人以较高数额赔偿、双方达成谅解后,最终依法不适用死刑的案例。其中有一起“邓永旺故意杀人案”,被害人家属索赔50万元,原审法院并未判决被告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到了死刑复核阶段,最高人民法院主持调解,被告人家属最终答应赔偿28万元,最高人民法院最终不予核准邓永旺死刑。还有一起“邓玉谱故意杀人案”,一、二审法院均判处附带民事诉讼赔偿“7353.5元”,后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被害人家属与被告人家属最终达成协议,一次性赔偿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对邓玉普不予核准死刑。这两起案件,前者是被害人提出50万元的高额索赔、但并未得到一、二审法院支持,后者是被告人家属最终支付了远远超出判决书认定数额的赔偿金。按照本案起诉书的逻辑,被害人只要提出或获得高于实际损失的赔偿金额就是“以非法占有没目的”,那么在上述案件中,最高法院和各级人民法院岂不都成了敲诈勒索的帮凶?!
4、就被告人张某个人而言,参与此事纯属朋友帮忙,其并无任何从中渔利或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张某虽然是律师,但参与此事,纯属为朋友无偿帮忙,就其身份而言,可以说是蔡某的代理人。就其参与此事的个人主观目的而言,并没有任何为自己获利的意图,更谈不上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对此,蔡某在2010年5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曾有明确陈述,两人从未谈及从8万元赔偿款中分给张某一分一厘的问题。
另外,就赔偿数额而言,是蔡某最先向对方提出了10万元的赔偿请求,张某作为朋友或者代理人,只是具体落实蔡某的索赔请求,通过与对方协商来寻求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他既没有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和请求,何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
因此,就张某个人而言,他仅仅是觉得蔡某的权利受到无端侵害,帮助朋友讨个公道,从未有从中收取一分钱好处的意愿,更谈不上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如果连这样的人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则法律和司法的公正性何在?!
(二)被告人客观上并未实施敲诈勒索意义上的“威胁或者要挟”行为,也没有逼使他人交付财物
敲诈勒索罪的客观方面,是采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惧怕,逼使对方交出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虽然一再声称“向公安机关告发”邹某,但该行为并不属于敲诈勒索意义上的“胁迫或者要挟”:
1、邹某的行为确实涉嫌刑事犯罪,蔡某作为被害人有权进行控告,这是其合法权利,不具有非法性
如前所述,邹某2010年5月2日晚的“故意撞车”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有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寻衅滋事罪”、“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故意伤害(未遂)”等罪名。作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蔡某,依法享有控告权,既可以向公安机关控告,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因此,无论其以何种方式“告发”邹某的犯罪行为,都是蔡某的合法权利,没有任何违法性。
至于邹某具体涉嫌何种罪名,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不同的理解,张某并非刑事诉讼律师,对刑事法律并不熟悉,不能要求他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一定要与立法精神或司法认定相吻合。因此,张某在参与此事处理过程中,即使说过“邹某涉嫌刑事犯罪,应被判刑”之类的话,也是有事实和法律根据的,并非凭空捏造2、被告人向邹某、桂某承诺“不再追究邹某刑事责任”,体现了轻微刑事案件可以自行和解的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正当性。
对于一些轻微刑事案件,允许当事人自行和解,是相关立法规定、司法文件和刑事政策的一致要求。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1月印发的《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和解,其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就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精神抚慰等民事责任事项进行和解,并且可以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要求或者同意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理达成一致”。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2月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40条也规定:“对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刑事案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理,依法定罪处罚。对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等轻微刑事案件,诉至法院后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应当予以准许并记录在案。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此类案件尝试做一些促进和解的工作。”可见,对于轻微刑事案件,相关司法文件不仅不反对当事人自行和解,而且大力提倡和解,并要求司法机关促进和解工作。
对于自诉案件的和解,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也有明确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诉。”虽然这是对已经提起的自诉案件自行和解的规定,但从中可以看出立法对自诉案件和解的态度:双方当事人在起诉前或起诉后,均可以自行和解。
本案中,邹某所涉嫌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故意伤害(未遂)罪,属于可公诉、也可自诉的轻微刑事案件。既然在性质上属于“可自诉”的案件,那么在公安司法机关立案之前,双方当事人不仅可以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和解,还可以就“是否追究对方刑事责任”达成一致。因此,被告人向邹某、桂某承诺“在赔偿8万元之后,不再追究邹某刑事责任”,是自愿放弃其刑事告诉权的体现,完全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综观本案全部事实,从5月2日“撞车”发生至5月25日报警案发,双方当事人其实一直在进行刑事案件的自行和解工作:一方面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协商,另一方面就是否追究邹某刑事责任达成一致。这种自行和解工作,完全是在现行立法和相关司法文件所规定的框架下进行的,具有完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怎么会构成“敲诈勒索”呢?!
3、在5月2日案发之初,被害人蔡某已经向公安机关110报案,告发行为其实在双方协商赔偿之前已经实施过
5月2日晚撞车发生时,蔡某已经报警,属地派出所和交通队民警都到达现场,随后进行了现场勘查和调查问话。在警方已经知情的前提下,鉴于邹某所涉嫌的罪名属“可公诉”案件范围,即使蔡某不再提出新的控告,公安机关在发现后也完全可以、甚至应当依照职权主动进行追究。
在此意义上,邹某、桂某害怕受到刑事追究,其实与蔡某是否再次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
4、“向公安机关告发”只是被害方维权的手段和技巧,并不具有强制性,最终的赔偿数额仍是双方自愿协商的结果,并非被告人逼取
敲诈勒索罪所要求的“威胁或者要求”,不仅要具有非法性,而且必须强制性。所谓强制性,是指被害人一方无可选择,只有接受对方提出的一切条件。而在本案件中,邹某、桂某一方并非无可选择,他们可以完全不接受蔡某一方的要价,转而让对方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纠纷。即使他们愿意通过协商方式解决,也完全可以不接受蔡某一方的要价,而提出一个自己认为可以接受的赔偿金额。事实上,在5月9日晚双方第一次见面协商时,是桂某首先提出“可以多赔一点钱”。而且,从最终情况看,8万元赔偿金也是邹某、桂某一方在不接受10万元的赔偿金额的前提下,通过讨价还价得来的,双方还当场签署了《协议书》。这显然是双方合意的产物,并非被告人“逼取财物”。
另外,从5月25日晚被害人一方主动报警的情况看,被告人的所谓“向公安机关告发”,实际上也不具有强制性。如果被害人一方果真“害怕邹某被追究刑事责任”,他们就不会选择主动报警。他们应该想到:一旦报警,邹某涉嫌犯罪的行为也就可能被对方告发,就可能真地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5、在5月25日晚签署协议时,蔡某提出把钱退给对方,却被对方拒绝
根据蔡某、张某的当庭供述:在5月25日晚双方见面签署《协议书》时,由于桂某、白某提出要查验张某的律师证等要求,蔡某有些不耐烦,随即把5万元现金拿到桌子上,推给对方,并说:“你如果不愿意,就把钱拿回去”,但却被桂某、白某拒绝。
这表明,如果桂某并非自愿付款,完全可以把钱拿回去,或者继续进行协商,或者通过公安司法机关介入处理此事。但奇怪的是:桂某、白某却拒绝坚决拒绝收回这5万元,而是劝说蔡某赶紧把钱收起来。这一重要情节,足以证明:蔡某、张某并未“逼取他人财物”,桂某也绝非被“威胁或要挟”而“被迫”付款。
(三)将维权行为定性为敲诈勒索犯罪,不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而且会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
1、维权过程中的索赔行为,是合法的民事行为,民事上合法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综合本案全部事实,被告人的行为基本上属于自身权利遭受非法侵犯后、所进行的正当维权行为,在手段和目的上均具有合法性、正当性。至于赔偿数额,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协商。从法律性质上说,在民事上合法的行为,不仅不具有违法性,而且也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从而根本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对于这种有“前因”的维权案件,即使权利遭受侵害的一方在维权过程了实施了一定的“过度”行为,甚至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威胁或者要挟”,刑法立法和刑事司法也应秉承其谦抑精神,谨慎介入,不应轻易入罪。
这一点,可以从当年广受关注的“黄静敲诈勒索华硕公司案”得到验证。黄静因所购电脑被置换了测试版CPU问题,向华硕提出50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要求,并声称如果华硕拒绝这一条件,将向媒体将此事公开。协商过程中,华硕公司报警,黄静被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刑事拘留,后被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批准逮捕。2007年11月9日,海淀检察院向黄静作出不起诉决定书(京海检刑不诉[2007]154号)。2008年9月22日,海淀检察院进一步作出刑事赔偿确认书:“黄静采取向媒体曝光、将华硕公司使用测试版CPU公之于众的方式与华硕公司谈判索赔的方式,虽然带有要挟的意味,但是与敲诈勒索中的胁迫有质的区别。黄静在自己的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并不是一种侵权行为,反而是一种维权行为,所要500万美金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海淀区检察院的上述认定,对于区分“维权过度”与“敲诈勒索”提供了典型范例。如果说黄静索赔“500万美元”都不是敲诈勒索,而是“一种维权行为”,那么本案被告人索赔“10万元”又如何能定性为“敲诈勒索”?!
2、如果判处本案被告人有罪,不仅有违罪刑法定,而且会产生极大的消极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不利于公民依法维权
如前所述,由于本案被告人在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没有实施敲诈勒索意义上的“威胁或要挟”,因而完全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入罪。如果强行入罪,则于法无据,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另外,如果判处本案被告人有罪,还将会产生极大的消极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广受关注的“黄静敲诈勒索华硕公司案”,最终以检察机关不起诉、国家赔偿而告终,被认为是为“维权”正名、伸张了正义,因而受到各界赞赏。本案判决,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必然会引起更大的关注和争议,损害司法机关的公正形象。另外,人民法院的判决还会对社会和人们的行为产生指导和规范作用,必须慎重进行。南京彭宇案就是典型的一例。2007年9月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一审判决书一经作出,立即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此后各地不断出现了“没有人敢扶老人过马路,看到老人摔倒也没人敢扶”的怪现象,引发了一场“公共道德危机”,有媒体评论说该判决导致社会道德水平倒退了几十年。
本案也是一起由于维权而导致的敲诈勒索案件,如果法院不能为权利受侵害的一方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而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则势必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并产生消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
恳请人民法院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
谢谢!
辩护人: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 毛立新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一日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