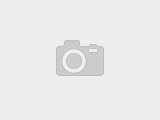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的顶层设计,但实践中如何具体把握还存在不少疑问。笔者认为,对法官审理错案实行“终身追责”,应当注意区隔“责任豁免”的情形。
具体来说:如果法官在审判的过程中存在牟取私利、有违中立地位的情形,甚至有收受贿赂、渎职、玩忽职守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应当“终身追责”,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刑事责任;如果法官只是在事实或法律适用问题的判断上发生了偏差而导致被改判或发回重审,应当“责任豁免”,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错案的发生是因为法官的违法违纪造成的;如果法官由于办案能力有所欠缺,经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差错,应当将其调离审判岗位。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司法权是判断权的本质属性必然包含了对判断主体可能犯错的包容性。
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语言本身的开放结构,都决定了事实与规则之间尚存距离,法官所要做的就是以他的知识、经验以及对社会价值和公共政策的把握来解释规则、明晰其适用的范围乃至在空白地带创设规则,只有这样,法律才获得生动性、再生力和可塑性,保持了与整个社会的同步。由此,法律适用绝非简单的逻辑涵摄,尚需要规范评价的联结,必须依赖价值判断。但“价值”是一种模糊的表达,价值评判本身即具有不可测度的特性,因此也不再是始终只有一个正确答案,这便是司法的规律之一。如果我们始终以监督法官对案件的判断“是否是错误的”为着力点来推进法官负责制,就会偏离司法的规律,司法所珍视的价值就自然会被实用主义、后果主义、功利主义所消解,司法“去行政化”的目标不仅无法达到,反而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司法的“行政化”。
第二,“错案”在内涵和外延上均具有一定的开放性,需要进一步细化。
从语义学分析,“错案”更多是一个社会通常用语而不是一个法律词汇,我国现行的法律也没有对“什么是错案”作出明确的界定,更多只是列举了上级法院可以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一些具体情形。“错案”既包括案件在事实判断、法律适用上有错误,也包括法官为牟取私利枉法裁判,还包括案件虽然实体处理没有争议但在程序上违法等各种情形。如果把这些情形都纳入“终身追责”的范围就显得过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第二章的规定,其将“故意和重大过失”为主观要件来认定违法案件或重大差错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错案追究”的范围。但也有学者认为该《办法》对“错案”还没有完全限定明确,比如对程序、实体处理上存在瑕疵的案件,如果通过二审、审判监督程序得以纠正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也应当明确不属于“错案”。但最起码该《办法》对于如何认定“错案”,提出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和尝试。
第三,对“错案”不作区分就“终身追责”,不利于法官职业群体自身的发展。
边际效应理论认为:一件事物总有其效用的边界,如果超出了这个边界,其效用就会不断降低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强调对法官枉法裁判的刑事违法性“终身追责”,事实上已经极大增加了法官违法的成本(因为就刑事追责而言,其本身也有追诉时效的限制),如果再任意扩大追责的范围,就可能打破依法履职与监督制约之间的平衡,对法官独立审判和自主性产生极大抑制,进而影响整体上司法功能的发挥。可以想象,如果法官每判决一个案件都要担心将来要被追究责任以至“终身负责”,法官就成了惊弓之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他可能会更多考虑如何把案件“解决掉”,而不是如何把案件“解决好”;当更多的法官都有这样的心理时,就可能形成一个缺乏自主精神、依赖感强、不太注重专业知识积累、不愿意承担责任、缺乏效率的职业群体。
第四,对一部分“错案”责任不予追究,并不必然导致更多更大的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
一方面,对一部分“错案”不予追责,是因为这部分“错案”实系法官的“无心之过”,与司法中立的根本问题无涉,但即便如此,这部分“错案”也还可以作为惩戒、纪检部门进一步核查的线索;另一方面,追不追究“错案”,与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之间也只是或然的条件关系而不是高度盖然性的或必然性的联系,要减少和杜绝司法不公正的问题,还需要法官职业准入、司法职业化建设、司法公开、法官职业保障等各项制度的共同推进。事实上,司法权力运作的受制性,不仅仅体现在对权力滥用后的查问,还包括对权力行使中的监督,如通过加强司法公开提升司法透明度也是一种制约手段,并且由于媒体技术带来的信息快速传播的优势,强调公众参与对司法的监督较之其他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还可能更为有效,也符合司法本身运作的规律。
总的来说,对法官实行“错案追究”和“终身负责”,必须要注意区隔出“责任豁免”的情形,只有当一个法官的具体的外在行为表现出对法官所必备的公信力、公正性的背离时,才能启动追究法官责任的程序。就此而言,发生“错案”只能是责任追究的必要前提,而不是充分条件。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