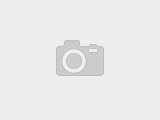司法需要判例
作者:何家弘

司法需要判例
2015年4月2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究(北京)基地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揭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慕平共同为基地揭牌。在随后召开的知识产权案例指导研讨会上,笔者应邀发言,以一个“外行人”(就知识产权法来说,我基本上不懂)的角度谈了几点想法。
第一,判例不等于判例法,也不等于案例。英国是判例法的发源地,也是最为完备的司法判例制度的发源地。大陆法系国家一般不存在判例法,但是也有判例。司法判例是包含着法律适用规则或法律解释理由的法院判决。判例来源于案例,但并非所有案例都可以称为判例。例如,警察机关和检察机关可以编发案例汇编,也可以发布指导性案例,但是这些案例不可以称为判例。
第二,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从世界各国法治的发展历程来看,大陆法系国家具有重视立法的传统,因此其法治建设是以立法为中心的,其制定法体系也达至较高的水平。英美法系国家具有重视司法的传统,因此其法治建设是以司法为中心的,其判例法体系也就达至较高的水平。不过,两大法系国家的法治发展都逐渐在较高水平上达到了立法与施法的平衡。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法治建设的重心一直是立法,从“无法可依”进步到“有法可依”。而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法律而无法治。要从“有法可依”走向“有法必依”,法治建设的重心就要从立法转向施法,包括司法。
第三,司法判例制度大发展有两种基本模式。英美法系国家所走的是从判例法到判例法与制定法相结合的道路,而大陆法系国家所走的是从制定法到制定法与判例相结合的道路。二者的路径不同,偏重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达致了制定法与判例制度的平衡。这种发展轨迹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四、中国司法判例制度的现状。在中国,制定法是基本的法律渊源,判例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没有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主流观点的认同。多年来,中国的司法机关和法律学者也编纂过多种案例汇编。然而,这些选编的案例对法官裁判没有拘束力,只是学习研究的参考资料而已。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1年12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一批4个指导性案例。至2015年4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一共发布了10批52个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的颁布,标志着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判例制度已初步建立,但是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第五,中国司法判例制度的缺陷。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的数量太少,很难满足司法实践中对于判例制度的需求。从世界各国推行司法判例制度的经验来看,判例的优势就在于数量众多和细致入微,因而比抽象概括的立法更便于司法人员掌握和适用。其次,这些指导性案例虽然是最高人民法院精选后发布的,但并不都是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审理的案件,其中有些案件是基层法院审理的。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例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之后便作为比审理该案之法院的级别更高之法院的“指导”,这种让“上级法院遵从下级法院”裁判的案例指导制度有违司法判例制度的一般原理。此外,这些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改编”的,并非“原汁原味”的判决。虽然这种做法可以实现指导性案例格式的统一并可能提高指导性案例的水平,但是不太符合司法判例的生成规律。再次,“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定位不够明确,“应当参照”的语义相当模糊。
第六,中国司法判例制度的完善。首先,明确司法判例的挑选标准。司法判例制度可以分为自然生成和人工选编两种模式。自然生成是司法判例制度的最佳模式,但是以法院判决的普遍性发布与汇编为条件。在当下中国,采用人工选编的模式还是较好的选择,但是要明确挑选判例或曰指导性案例的标准,例如,判例应该是二审法院和再审法院的判决,案件中的争点应该是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已经就相同的法律争议问题作出两次以上的裁判等。其次,规范司法判例的发布程序。指导性案例不宜“少而精”,而应“多而全”,因此,指导性案例的发布程序应该简化。再次,明确司法判例的效力。例如,我们可以借鉴欧陆模式,通过审判管辖权和审级制度来维护指导性案例的拘束力。例如,本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对后案裁判具有拘束力,上级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对下级法院的后案裁判具有拘束力,最高法院的指导性案例对全国法院的后案裁判具有拘束力,而这些拘束力的维系主要依靠上诉审和再审的制度。
综上,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司法判例制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司法者群体自由裁量权的张扬;另一方面,它又是司法者个体自由裁量权的约束。二者在具体国家中的平衡,体现了司法判例制度的完善程度,也体现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发展水平。
(本文内容摘自作者发表于2015年第1期《法制与社会发展》的“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需要”。)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