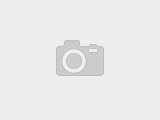当前我国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的困境及其权利保障
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 吴情树

刑事辩护律师
内容摘要: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拓展了律师的辩护权利,缓解了律师执业中一些困难,有利于提升刑事案件的辩护质量。但是,由于立法本身的不配套,加上传统司法惯性的影响,司法环境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这些难题反过来又影响了刑事辩护活动的开展,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因此,在未来中国法治的建设中,律师应该积极参与推动中国司法改革,以便国家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氛围,共同提高中国法治的水平。
关键词:刑事辩护 执业困境 权利保障
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极大地拓展和保障了律师的辩护权利,缓解了刑事辩护中长期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有利于提升刑事案件的辩护质量,从而有效地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一年后,针对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2014年期间,全国各地法院纷纷出台文件,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禁止对律师进行歧视性安检,并于2015年1月29日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复核案件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办法》,强调应充分发挥控辩审三方职能,加强律师在审判中的作用,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辩护权利。此前,2014年1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颁发了《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六个方面强调要依法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包括依法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阅卷、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权、提出意见的权利、知情权以及律师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代理权。但在现实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律师的执业权利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尤其在刑事辩护中仍存在着诸多困难。其中缘由,既有立法的不明确和不配套,也有司法环境使然。本文根据我们对司法实践的观察,结合我们辩护的经验和体会,简单地列举目前刑事辩护所存在的困难及其存在的原因,以期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逐步加以解决。
一、律师在个别案件中的会见权仍然存在某种障碍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37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辩护律师持“三证”就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超过48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也应当经侦查机关的许可。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发的《决定》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除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外,其他案件依法不需要经许可会见。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出会见特别重大贿赂案件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和相关规定及时审查决定是否许可,并在三日以内答复;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在会见时不得派员在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监听律师会见的谈话内容。
可以说,绝大多数普通刑事案件中,律师的会见权已经不存在任何障碍,尽管有些地方的看守所需要提前预约。但在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三类犯罪案件以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中,由于刑事诉讼法规定,这种会见要经过侦查机关的许可,但侦查机关由于考虑律师介入之后,会影响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影响他们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侦查机关是不会许可的,或者以各种理由予以拖延。在这些案件中,律师的会见权就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是剥夺。
二、律师在个别案件中的阅卷权仍然无法得到保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卷宗材料。《决定》第6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障律师的阅卷权。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人民检察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经人民检察院许可,诉讼代理人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受理并安排律师阅卷,无法及时安排的,应当向律师说明并安排其在三个工作日以内阅卷。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检务公开的相关规定,完善互联网等律师服务平台,并配备必要的速拍、复印、刻录等设施,为律师阅卷提供尽可能的便利。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应当在人民检察院设置的专门场所进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员在场协助。
在大多数案件中,辩护律师的阅卷权一般都能得到保障。但在个别、少数敏感案件或者在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证据材料还不那么确实、充分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往往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律师阅卷。例如,检察机关往往会以案件需要进一步补充侦查或者案件的卷宗材料还不齐全为由,不让律师阅卷,这就限制和剥夺了律师及时阅卷的权利,律师无法阅卷,就无法知悉案件情况,更不要说发现案件在证据和事实认定上到底存在着什么问题,于是,也就无法及时向办案机关提出辩护意见。
三、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申请调查取证权难以有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9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398条规定:“在审查起诉期间,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辩护人的申请,向公安机关调取在侦查期间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2013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24条规定: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辩护人申请调取可能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的证据,应当准许。《决定》第7条第三款规定: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人民检察院收集、调取证据,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决定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决定不予收集、调取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律师可以在场。
根据这些规定,办案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具有客观公正的义务,必须全面收集有利于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规定几乎变成了一种“乌托邦”的设想,因为检察机关同时又是公诉机关,天生就有胜诉的冲动和追求,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决定了他们在证据的收集和调取上,更倾向于收集或者调取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因此,当律师申请检察机关去收集或者调取有利于被告人证据的时候,检察机关的积极性并不是很高,也不是非常重视。如果案件到了法院审判阶段,律师向法院申请调查或者收集证据,法院一般也不会亲自去收集或者调取这些证据,往往也是通过检察院来收集或者调取证据。
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长期存在着“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司法理念,司法机关在收集和调取证据中,更倾向于收集、调取不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罪重的证据,而不喜欢收集、调取有利于被告人无罪、罪轻证据,甚至在个别案件中,还会隐匿、销毁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罪、罪轻的证据,即使辩护律师已经向检察机关、法院申请调取有利于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甚至已经为其列出了一系列证据清单,他们积极性也不高,并没有兴趣去收集和调取这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而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检察机关的客观义务,也与法院中立、超然的地位不相符合,《刑事诉讼法》要求办案机关全面提供证据的程序就此失灵了。
四、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启动比较艰难
为了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发生,《刑事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第56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权申请人民法院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依法予以排除。申请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证据的,应当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
在刑事诉讼中,在律师通过与嫌疑人、被告人的会见,往往就能了解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是否遭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如果有可能遭到刑讯逼供,辩护律师就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启动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要求检察机关担当起法律监督的职能,以确保侦查机关取得证据的合法性。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个程序的启动还是比较艰难的,一方面,由于辩护律师没有技术侦查权,一般难以提供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另一方面,即使提供了,相关的检察机关、法院不愿意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他们宁可相信公安侦查机关所出具的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工作说明”,也不会相信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活生生”的证据材料,因此,他们也就难以启动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除非这种刑讯逼供已经导致嫌疑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严重后果或者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即使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院也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采纳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明侦查行为合法性的材料和说明,一般也不会轻易排除这些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更不会由此判处被告人无罪。
五、证人(警察、专家)出庭“作证难”
长期以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难一直是个大问题,在绝大多数的案件审理中,证人都不出庭,而是由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证人证言,好像办案机关调取、收集的证据先天就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先天就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相反,由于有刑法第306条的存在,许多律师不敢接触证人,更是不敢去找证人调取、收集、核实证据,即使有去找证人调取、收集、核实证据了,为了避免被公权力机关说成是帮助证人伪造证据或者改变证言,许多律师都要带录音录像设备,进行同步的录音录像,甚至还要请公证处的公证人出来做公证,以免日后遭到牢狱之灾,这就是当前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的最大风险,也是律师不敢轻易亲自找证人进行调查取证的原因,尤其是在受贿罪案件中,个别行贿人是在办案机关的威逼利诱下做出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证言,一旦做出证言之后,又后悔了,在律师找他们重新调查、核实证言的真实性,并重新作证言笔录,在将这些证言笔录提交给法院之后,检察机关就会认为证人是受到律师的蛊惑或者引诱才改变证言的,其证言不具有真实性。言下之意,只有检察机关自己做出的证言才具有真实性,律师做出的证言就不具有真实性,这是一种执业偏见,并不是每个案件都是如此。因为在许多办案机关人员看来,律师更善于伪造证据、教唆、引诱证人改变证言,从而导致证人证言的虚假性。
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销毁、隐秘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威胁、引诱证人做虚假证言的更多还是公权力机关的办案人员,如公安机关或者反贪局,他们依赖着国家的强大后盾,为了拿下案件,赢得胜诉,总是会千方百计地获取证人证言或者其他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在我国这几年平反的冤假错案中,有哪个冤假错案不是由公权机关制造出来的?大家有听说过律师造假案、错案的吗?这样,由于证人不能到到庭接受法庭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质证,不能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盘问,其证言的真实性就难以得到证实,一些案件的庭审也就流于形式,开庭变成走过场,毫无意义。因此,在我国进行司法改革和推进“庭审中心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强化庭审的实质意义,在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尤其是真伪难以判断的案件中,更要重视证人的出庭作证的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二款规定: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第三款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88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第二款规定: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被处罚人对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
尽管《刑事诉讼法》有关证人出庭作证做了这么多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制度仍然难以得到贯彻实施,从而使得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沦为一句空话。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的规定,证人要出庭作证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二是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三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在这个三个条件中,由于设置了“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这样的条件,使得证人出庭作证的制度很容易被规避而变得形同虚设。因为在许多案件中,尽管律师提出该证人的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但法官仍然会以该证人证言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没有重大影响为由或者觉得证人出庭作证很麻烦,从而认为没有必要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换言之,证人是否出庭作证,完全由法官自己说了算。因为“什么是必要”,“什么是不必要”,目前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完全交给法官自由裁量,法官说有必要就是有必要,法官说没有必要就没有必要,这样,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没有得到任何限制和控制,律师的权利也没有什么救济途径和措施,而只能眼巴巴地听着“法官说没有必要”。
因此,笔者建议,为了提高证人出庭率,为了有效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最高法院有必要对刑诉法第187条中“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做出明确的解释,并列举一些必要的标准,否则,这个条文就难以发挥作用,增加证人出庭率就是一句话空话,冤假错案就很容易发生。
六、律师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或者羁押必要性审查难以有效果
修正后刑事诉讼法为了保障逮捕羁押的准确性,降低刑事案件的羁押率,不仅明确规定了逮捕的条件,还规定了审查逮捕的律师参与制度,甚至还明确规定了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这些程序的规定无疑可以限制检察机关随意启动批准逮捕程序,让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的时候更加慎重,以此可以降低目前居高不下的羁押率,有效地保障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同时,也拓展了律师辩护的空间。例如,《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一些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例如,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辩护律师没有提出要求的,检察机关只是可以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这个“可以”意味着,如果律师不知道案件已经报送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而没有及时提交辩护意见书,或者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聘请律师,检察机关可以不听取,也无法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更值得深思的是,由于法律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有事先通知辩护律师的义务,使得他们在进行审查时,往往可以避开律师的辩护意见,在辩护律师提交辩护意见之前,恣意地做出逮捕的批准,这就使得审查逮捕的律师参与制度的功能大打折扣。只有在嫌疑人、被告人有聘请律师,并且律师已经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才是“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同时,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对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也没有真正贯彻到底,理由很简单,对于什么是“不需要继续羁押”,《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能根据逮捕条件和其他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来判断什么是“不需要继续羁押”。例如,嫌疑人、被告人突然患病或者怀孕等可以变更为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除此之外,一旦检察机关做出了批准逮捕决定,要让他自己推翻原先的批准,简直是难上加难,因为检察院自己是决定、批准逮捕机关,在刑事拘留或者批准逮捕上,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自己就是决定机关,不存在中立第三方的裁决机构,不符合诉讼的构造,因此,这些行为就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诉讼活动,律师的辩护也就难以称得上法律意义上的辩护行为,因为辩护是针对指控而言的,在指控与辩护之间,必须存在中立的第三方裁决机构,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然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变更强制措施。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不管是刑事拘留,还是逮捕的批准或者决定,都是由办案机关一方说了算,检察机关一旦做出逮捕批准,要让他们再次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并且变更强制措施,简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让他们打自己的嘴巴,同时,这种不符合诉讼构造的行为完全违背了“自己不能当自己案件法官”的原则。这应该是律师申请启动羁押必要性审查或者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均难以奏效的法律原因,同时也是检察机关做出逮捕批准后难以自行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的法律原因。
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司法惯性的影响,“逮捕是定罪的前奏,量刑的预演”,逮捕的证据条件和定罪的证据条件几乎是等同的,被告人一旦被批准逮捕,那么,要求办案机关变更强制措施很难,案件流程就会自动地运转下去。如上所述,主要原因在于决定或者批准逮捕并没有外在力量的制衡和监督,逮捕或者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没有采取诉讼化构造,没有第三方的中立机构进行裁断。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自己就充当裁判者,使得指控者和裁判者合为一体。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假如原告本身就是法官,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充当辩护人。”
此外,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嫌疑人、被告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尤其是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权利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和实施,理由就在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应当变更强制措施而没有变更,应当取保候审而拒绝适用的诉讼决定,没有确立任何程序上的法律后果,尤其是没有针对那些违反法律程序任意延长未决羁押的行为,确立专门的诉讼行为无效机制,更没有对侦查人员滥用未决羁押的行为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但司法实践中,一些办案机关根本不理会,也不做出书面答复。
作者简介:吴情树,福建泉中律师事务所律师,福建省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泉州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