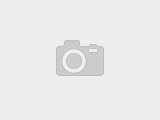近几年,敲诈勒索罪已然成为高发罪名。其中上访、职业打假、消费维权领域为高发领域。法律条文规定简单,但现实生活纷繁复杂,致司法实践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分歧较大,时常出现“同案异判”情况。如上访,“政府”能否成为敲诈对象不同法院认定不一,再如“公布隐私、检举揭发”等手段是否构成敲诈,亦存在争议。但近几年有关敲诈勒索较为轰动的案例中,均经历了从有罪——无罪的过程,可管中窥豹,司法理念在逐渐革新,对敲诈勒索罪的认定愈加慎重。
相关无罪案例
黄静华硕天价赔偿案,黄静发现购买的华硕电脑CPU存在问题后,以向新闻媒体曝光为威胁,向华硕公司要求500万美金的“惩罚性赔偿”。谈判过程中,华硕公司以敲诈勒索为名向公安报案,但此案最终以检察院不起诉终结。检察院认为黄静在自己权益遭到侵犯后以曝光的方式索赔虽带有要挟意味,但并不是一种侵害行为,而是维权行为,索要500万美金属于维权过度但不是敲诈勒索 。
永州陈曙光案,陈曙光以向10086及信息产业部投诉为威胁,先后与七家电信增值业务商(简称SP商)进行协商,要求高额赔偿。一审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二审维持。后再审法院以陈曙光虽具有超倍索赔故意,也具有超倍索赔行为,虽其行为带有“要挟”意向,但事出有因,改判其无罪。
沈光朗敲诈勒索案,沈光朗号召团队成员以发送恐吓短信、威胁邮件(例如在大陆花五万买下一个人头)、律师函、匿名检举信等方式要求老板蔡得支付公司上市奖励,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后再审法院以其存在合法债权债务关系、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为由改判沈光朗无罪。
“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敲诈勒索案,郭利在雅士利公司上市期间,向多家媒体揭露施恩公司不利信息,获得赔偿款40万元,并承诺“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后郭利继续接受媒体采访,并再度提出300万赔偿要求,施恩公司在与郭利谈判期间报案,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后广东高院认为郭利行为尚未超出民事纠纷范畴,不足以证明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亦不足以证明其实施过敲诈勒索的行为,改判郭利无罪。
苏晔绯敲诈勒索案,此案为笔者跟随王万琼律师、游飞翥律师办理。一审法院认为苏晔绯以举报为胁迫、索取股权转让款判其有期徒刑三年,二审辩护人介入后经综合评估以苏晔绯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对股权转让款享有正当权利为主要辩点,最终此案检察院撤诉退回公安,苏晔绯终获无罪。
纵观该些案件,是否构成敲诈勒索,最终落脚点均在于是否具有“目的正当性”。在目的正当的大前提下,尽管索要金额过限、手段非法,也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当然,如若触犯其他罪名,可以相关刑罚进行规制。
分手费、青春损失费是否具有目的正当性?
目前我国民法并不承认“分手费”、“青春损失费”的合法地位,但刑法的认定标准有别于民法。刑罚作为最严苛的惩罚手段,轻则剥夺人自由、重则剥夺生命,入罪应极为审慎,即使不符合“公序良俗”,在不触碰法律红线的情况下,其正当性仍应予以肯定。
若男女双方自愿签订相关“分手费”、“青春损失费”等补偿协议,女方进行索偿,具有理所当然的正当性;若双方未签订相关协议,女方单方索偿,单方认为其有过巨大付出及牺牲,真诚地认为自己存在索偿的权利基础,若是正常男女恋爱关系,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在婚外情中,尽管违背法律对“一夫一妻制”的保护,也不符合大众道德观,但仍属于“事出有因”,仍具有一定目的正当性,不应以犯罪进行评价。
(笔者注:两性关系中,双方对分手费、青春损失费、夫妻“忠诚协议”等类似约定,以“赠与”形式约定更能获得法律上的支持。)
以公布隐私为威胁是否构成敲诈?
曝光、举报、控告等手段被频频认定为敲诈手段,但究其实质而言,该些手段本身具有合法性。如消费维权中,曝光手段属于正当行使监督权的行为,可被看作民事领域主张索赔的策略之一,实质并不具有强制力。若商品质量着实存在瑕疵或是缺陷,其理应受到舆论谴责甚至是法律惩处;若曝光者歪曲事实、虚构真相,则应以相关法律手段加以规制。当然前提都为具有“目的正当性”,若曝光者是为获得不受法律保护的非法利益,则其行为则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威胁或要挟”手段。
就吴秀波事件而言,若女方仅只就公布隐私为威胁,其是否公布、如何公布属于其言论自由范畴。若吴秀波行为符合公序良俗、道德标准,即便女方公布隐私,也不会导致其名誉受损,更不会造成其心理威胁;若其行为不符合道德伦理,究其源头,真正责任者应为其自身,而非曝光者。吴秀波作为公众人物,在享有其公共身份带来的巨大利益时,也应承担相应风险与代价。
(此案中,除曝光威胁外,从吴秀波妻子所发声明看来,极可能伴有持续不断威胁、骚扰、恐吓等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则应具体分析。)
金额过限是否构成敲诈?
金额是否明显过限,没有规范标准参考,不同案件情况不一,难以量化。但金额过限显然已经成为大部分维权型敲诈勒索案的重要入罪特征之一。
如上文所述黄静华硕天价赔偿案中,黄静索赔500万美金,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三倍赔偿标准,显然属于“天价索赔”,但在商品确具有瑕疵,且索赔人具有正当权利基础上,即便金额过限,也不应认定为犯罪(陈兴良教授观点)。目前司法实践也越来越倾向于此认定,如永州陈曙光案、“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敲诈勒索案中,因事出有因,最终都被认定为过度维权,而非敲诈勒索。
当然,权利人单方捍卫自己的权利也应有“尺度”与“边界”,对于此类过度维权行为,该如何规制,值得探讨。
总之,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全面、综合衡量,在敲诈勒索罪中,其与合理行使权利的关键节点在于是否具有“目的正当性”,在具有“目的正当性”的情况下,即便金额过限亦或是手段非法,也不应轻易入罪。
就吴秀波而言,究竟是舍弃自身声誉亦或是支付巨额“分手费”,这是其作为公众人物违背公众形象后所应承担的两难代价,无论其作出何种选择,都是基于其自身价值评估与利益衡量的结果。
刑罚作为社会管控的最后手段,理应保持其谦抑性,现今经济生活领域纠纷愈加复杂化,司法对于此类纠纷入刑应愈加谨慎,不能因为管理的方便和刑罚的威慑力,一味以刑罚来维护秩序。紧跟社会发展潮流,及时更新司法理念,让法律的归法律,让道德的归道德,才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