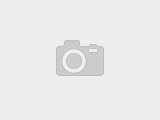在我国,三中、四中全会以来的多项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均明确要求建立值班律师制度。与此相适应,为推动值班律师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相关部门也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值班律师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立足现有规范性文件,有关值班律师制度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受到法学界的重视,并呈现以下两种基本倾向:
第一,有关值班律师制度的研究,大多以当前的认罪认罚改革试点为实践依托,着眼于探讨“如何更好地发挥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积极作用”。对此,有学者概括指出,“在所有的讨论中,关乎值班律师参与效果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是,应该如何合理确定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换言之,值班律师究竟是否辩护律师?”(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六期)在此研究脉络下,值班律师是否属于辩护律师?是否享有阅卷权、会见权等辩护律师的基本权利?值班律师的“准辩护人化”等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第二,受上述研究思路影响,有关值班律师制度的研究,其焦点在于认罪认罚案件中值班的“律师”,而不是法律援助制度之下的“值班律师制度”。但是,应当承认,作为一种特殊性的法律援助形式,值班律师制度旨在弥补传统法律援助服务的不足,而不是取而代之。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值班律师制度建设应当置于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一大背景下予以统一考量,而不是游离于法律援助制度之外,根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客观需要,探讨值班律师制度的“中国式改良”。(谭世贵、赖建平:《“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值班律师制度的构建”研讨会综述》,载《中国司法》2017年第六期)然而,在只见“值班律师”不见“值班律师制度”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如何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而不是如何推动“值班律师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衔接、相得益彰。
受上述研究倾向影响,有关值班律师制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当前值班律师制度建设亟待深入讨论的两个问题:
第一,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为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值班律师是不是一种“应然的制度选择”?
应当承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理论界与实务界已经就以下问题达成了普遍共识: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正当程序保障出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有序推进离不开辩护律师(尤其是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率尚在30%左右,70%左右的刑事案件还没有律师参与辩护。特别是速裁程序和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刑事案件,当事人自己聘请律师及获得常规法律援助律师的几率很有限。在此情形下,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却采用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程度较低的速裁程序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处理大量案件,不仅程序正义难以彰显,而且实体正义也难以保障。”(顾永忠、李逍遥:《论我国值班律师的应然定位》,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7年第四期)另一方面,从有效辩护的立场出发,也普遍承认,“值班律师在提供有效法律帮助方面必然存在一定的缺陷”(姚莉:《认罪认罚程序中值班律师的角色与功能》,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六期),“律师辩护的有效性则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熊秋红:《审判中心视野下的律师有效辩护》,载《当代法学》2017年第六期)。
然而,有趣的是,基于上述共识,相关研究成果不是反思值班律师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之间的契合性问题,而是立足现有规范性文件,转而讨论如何赋予值班律师更多的权能,并试图通过改造值班律师制度,以期使其更好地满足认罪认罚案件的现实需要。
很显然,上述改革思路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为了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值班律师制度是不是一种适宜的制度选择,或者说,是不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应然方向”?理论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解决司法实践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路径应当契合制度的一般发展趋势和规律,从而让制度发展的每一步都能够发挥一定的“积薪作用”。因此,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中,我们更需要的是关于值班律师制度是不是“应然”制度选择的正当化追问,而不是囿于规范性文件设定的框架,超出值班律师制度的本意,赋予其自身难以承载的额外权责与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全国人大公布的刑事诉讼法草案第34条第三款关于值班律师的规定,陈光中教授指出,对于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认罪认罚案件,传统的法律援助方式才是一种更为适宜的法律援助形式。其理由有二:“一方面,认罪认罚制度现在作为一个基本原则来规定,贯彻刑诉全过程,我本人表示支持。由此,认罪认罚案件的范围包括所有被判处重刑及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认罪认罚的案件除了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以外,其他通常都是三年以上的。这类案件诉讼程序简化但涉及被告人的重大利益,应当加强辩护权的保障。另一方面,《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中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案件、二审案件、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依照此规定,不仅只能在审判阶段提供法律援助,而且只适用于普通程序,不包括简易程序,总体来说范围较窄。因此,根据上面两方面的情况和四中全会提出‘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的要求,为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辩护才能满足需要。虽然力度有点大,但是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不是脱离现实的要求。对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也是世界法治国家和地区提供刑事辩护法律援助的最低标准(参考美国、加拿大、德国、韩国、台湾地区等地有关规定)。”
很显然,从法律援助制度体系化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律师参与,无疑更有助于解决认罪认罚自愿性的制度保障问题。
第二,在值班律师制度建设中,值班律师在刑事诉讼早期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未能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应有重视。
值班律师制度是一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偿提供及时性、临时性法律帮助的法律援助形式。因此,在英国司法实践中,值班律师发挥作用的场域,已经逐渐从治安法院的初次聆讯转移到了刑事诉讼早期阶段的警察羁押询问。在我国,根据2017年两院三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的意见》第2条的规定,值班律师的职责可以大体分为两类:值班律师的一般职责以及值班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特殊职责。然而,有关值班律师制度的研究无疑过于偏重值班律师如何参与认罪认罚案件的研究,而忽视了值班律师的一般职责。受此影响,如何更好地发挥值班律师在刑事诉讼早期阶段的作用,如何让看守所值班律师工作站更好地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及时性、临时性法律帮助等问题,一直没有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应有重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