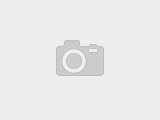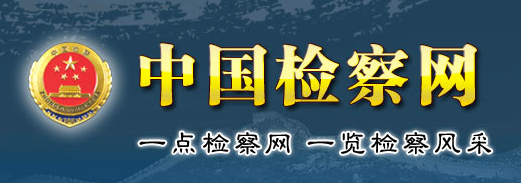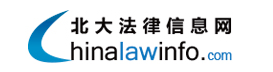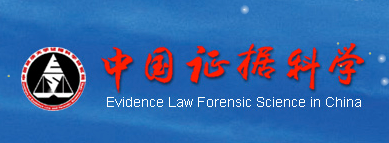近日一则wephone创始人苏享茂被前妻翟某某逼索巨额钱款后自杀身亡的消息刷屏,据传在此之前,翟某某曾以苏享茂存在个人漏税和网络电话产品属于非法经营灰色地带,要向公安举报为由向其索要巨额财产。结合现有公开材料,我们对这一事实中可能涉及的刑事法律问题从定罪量刑两个角度进行初步分析,供诸法律同仁批评。
一、翟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该条文并没有详细说明何为“敲诈勒索”,目前对这四个字只存在学理解读,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索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翟某某的行为如果构成此罪,需要在主客观方面满足以下要件:其一,翟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苏享茂实行了威胁,从而使苏享茂产生了恐惧心理;其二,苏享茂基于该恐惧心理处分了财产;其三,翟某某取得该财产,苏享茂遭受了实际损失。
从现有微信聊天记录和离婚协议,似乎从表面上看翟某某的行为符合此罪构成要件,但基于审慎判断的考虑,仍然有几项事实需要证据进一步证明或证否:
一是现有证据并不能排除翟某某的行为属于合法权利行使的合理怀疑,主要体现在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并没有完全划分清楚,虽然“离婚协议书”中存在“双方婚后无共同财产”的表述,而且离婚协议也显示双方从离婚到结婚才一个多月,存在大额共同财产的可能性较小,但不排除苏享茂在婚前存在其他处分财物如赠与的行为,囿于篇幅,婚姻法问题此不赘述。
二是现有证据不能完全证明苏享茂签订离婚协议或处分财产是完全基于恐惧心理,如果有证据证明苏享茂签订离婚协议或处分财产是完全基于对翟某某的精神补偿而非恐惧心理,在因果关系上就不能对翟某某进行犯罪评价。此外,网上盛传了一份苏享茂自杀前的陈述,这份陈述可以通过证明苏享茂主观心态而作为指控翟某某构成犯罪的证据,但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此份陈述应当作为“电子数据”而非书证或者被害人陈述进行举证、质证和认证,其次,此份证据的真实性必须经受刑事诉讼程序的考验。
因此,翟某某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终归还是属于事实问题,需要确实、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需要额外予以说明的是,以恶害相通告,与恶害实现本身的违法性与否并不存在关联。该事实中,即使苏享茂的相关业务涉嫌违法,本人存在偷漏税款的行为,对于翟某某行为性质的定性并不构成任何影响。
二、如果根据证据可以证明翟某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翟某某具有哪些量刑情节?
(一)法定刑档次的确定
从刑法条文我们可以发现,敲诈勒索罪被归入数额犯罪,即以犯罪数额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要素,从而反映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一类犯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二千元至五千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显然,如果单纯从数额上进行考量,该事实中“1000万+房产”就已经使法定刑档次毫无疑问达到了“数额特别巨大”的量刑档次。但这种评价法定刑档次的方式其实会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这笔钱究竟能否全额认定,是否存在应被扣减或刨除的部分,仍需要进一步挖掘相应的事实。
(二)量刑情节的认定
该事实存在四个量刑的情节值得探讨:
1、苏享茂自杀的后果是否构成法定“严重”或者“特别严重”情节?根据《解释》第四条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七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数额达到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百分之八十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解释》第二条第三项至第七项是指:“(三)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人敲诈勒索的;(四)以将要实施放火、爆炸等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或者故意杀人、绑架等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的;(五)以黑恶势力名义敲诈勒索的;(六)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七)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该条文没有将被害人自杀列入具体情节之一,但不排除将其归入第七项兜底条款之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司法解释本条文对于犯罪情节的认定仍然是与犯罪数额相挂钩的,这与我国数额犯罪认定的司法传统相契合。回到本项事实中,如果犯罪数额全额认定,则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与否,仅决定在十年以上法定刑量刑幅度的基础上是否从重处罚,而对法定刑幅度本身并会不构成任何影响。
2、翟某某是否存在“利用或者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人、新闻工作者等特殊身份敲诈勒索的”的情节?疑似苏享茂撰写的网上材料曾提到,“翟某某曾向其声称可以利用亲戚舅舅(公安局不小的官员)关系可以让他的产品下架,让苏享茂倾家荡产。”这一事实如果查证属实,应当根据《解释》第四条规定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而且如果翟某某舅舅确实存在警察身份,且参与其中,应当作为共犯处理。
3、翟某某的行为是否可以适用《解释》中关于敲诈近亲属的条文规定?《解释》第六条规定,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一般不认为是犯罪;认定为犯罪的,应当酌情从宽处理。本事实中,可以料想的是,翟某某获得苏享茂家属谅解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翟某某作为近亲属能否酌情从宽处理,就成了解释条文解读的范畴。该条文的表述确实存在一定争议,究竟应当理解为“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财物,...认定为犯罪的,应当酌情从宽处理。”还是理解为“敲诈勒索近亲属的财物,获得谅解的,...认定为犯罪的,应当酌情从宽处理”?获得谅解是否是酌情从宽处理的必要条件?与其盲目分析,我们不如比照一下其他司法解释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诈骗近亲属的财物,近亲属谅解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诈骗近亲属的财物,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具体处理也应酌情从宽。”该条文的表述十分明确,也就是说,与近亲属相关联的涉财物犯罪,取得谅解与否并非酌情从宽处理的必要条件。回到本事实,敲诈勒索罪与诈骗罪在侵犯家庭成员财产权利这一犯罪客体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解释》第六条同样应该比照诈骗罪司法解释条文的规定处理,翟某某这一酌情从宽行为应可以认定。
4、如果本事实中只是签署了离婚协议,没有任何款项交付、财产移转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本事实中并没有出现真实的款项往来记录或房产登记材料,仅有一份离婚协议成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协议本身并不具有财产价值,但由于其所记载内容体现债权债务关系,代表着财产性权利,该协议是否可以成为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对象,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债权属于相对权,财产所有权属于绝对权,前者的实现一般需要他人配合或者法院强制执行,而后者不需要。因此取得协议本身并不意味着必然取得财产所有权。协议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其意义在于证明债权债务人之间存在着权利义务关系,如果苏享茂或其家人以协议系胁迫签订为由抗辩,抗辩成立后翟某某并未通过协议取得实际的财产权。在此过程中,翟某某胁迫苏享茂签订了协议,并不仅仅是为取得财产准备条件,而是具体实行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只是因为客观原因而没有实现财产性利益。由于敲诈勒索罪是行为犯,因此应当认定翟某某构成敲诈勒索的犯罪未遂而非仅仅的犯罪预备。根据刑法规定,属于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本事实涉及刑法问题的分析告一段落。当然,对这一事实的判断只结合了现有证据情况,证据的真实性可能存在疑问,而且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有理由怀疑现有证据所反映的事实可能存在极大的价值倾向性,在没有听到翟某某的回应或者看到其他可能有利于翟某某的证据之前,仍然必须奉行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能对翟某某的行为作出是否必然构成犯罪的评价。
最后,还是应该对这位IT行业创业者致以最沉痛的哀悼——悲剧已然发生,无关结论几何,终归死者为大,愿苏享茂天堂安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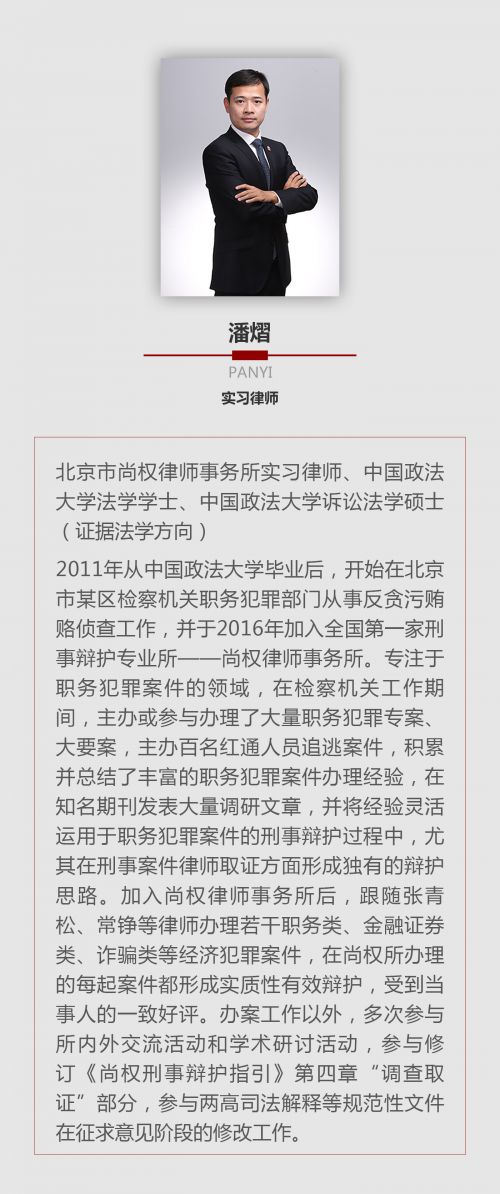
潘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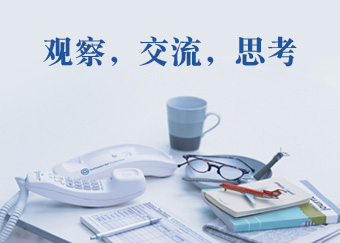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