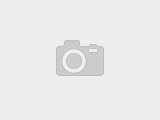陈瑞华:法院为何不敢做无罪判决

陈瑞华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9期总第538期,作者段文(凤凰周刊记者)。录音整理:实习生张玛睿。
15年前的2000年夏天,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出版了一本针砭大陆刑事司法制度弊端的专著——《看得见的正义》,书名来源于一句法律格言:“正义不仅要实现,还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也就在那年夏天,昆明警察杜培武走出了监狱大门,他此前因为涉嫌杀妻被判处死缓,服刑期间真凶出现,他无罪释放重获自由。随着杜培武的获释,一个骇人听闻的“警察对警察的刑讯逼供”冤案成为舆论焦点,如何防止、纠正冤假错案也成了社会热点话题。
十五年来,继杜培武案之后,佘祥林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等诸多刑事冤案不断曝光,每一次都引发诸多讨论,官方也不断制定相关政策、规定,修改法律出台司法解释,希望有所改进。
十五年间,陈瑞华作为一个资深学者,就冤假错案问题曾多次接受媒体采访或撰写相关评论文章,也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相关部门邀请提供专家意见。
15年后,当《凤凰周刊》记者就这一话题提出采访请求时,陈瑞华一开始却是出奇地沉默,然后反问:“你觉得这个话题还有什么可谈的?”
多年来,关于冤假错案的问题,无论是“司法独立”“权大于法”等制度性问题,还是“禁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等技术性问题,其实学界无一没有探讨过。
“但问题解决了吗?”陈瑞华指出,中国大陆多年的刑事司法体制,公检法已经形成固定的流水作业式的实践模式,这个总体格局不改变,解决刑事司法的公正性问题仍然任重道远。“冤假错案就个案而言,看起来都有一定偶然性,但其本质上是结构性问题,是中国刑事司法病症的总爆发。根子问题不解决,冤案发生就是必然的。”
法院为什么不敢做无罪判决?
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最高法院等相关部门也陆续出台了诸多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定,避免错误判决造就冤案,为什么实践中看起来收效甚微?
陈瑞华:我先反问一个细节,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在一些冤案被平反之后,相关法院的负责人对案件总结时,居然称“法院是有功的”,因为之前法院办案是“奉命行事”,但法院最后“刀下留人”,才使得当事人还能活着等到冤案昭雪。这种说法不觉得可笑吗?
法院要想防止冤假错案,他得有一个能力,能够说“不!”敢于宣布无罪。但大陆的法院能做到吗?你们看看近年来大陆法院宣判无罪人数的数字,无罪率到什么程度了?十几年前,全国各级法院全年几十万刑事案件,判无罪的数千人;到了最近几年,刑事案件数量一年超过百万了,但判无罪的人才多少?不到九百个。按这个速度发展下去,20年后,中国大陆还有无罪的判决吗?我把这称为“惊心动魄的数字”。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表明了什么?大陆的法院,从基层到最高,已经越来越不敢做出无罪判决了。但问题在于,刑事案件的质量在提高吗?犯罪嫌疑人真的都有罪吗?恰恰相反,那么多冤假错案表明,公诉案件只要一进入司法程序,结果几乎注定。
从这个角度而言,大陆的法院在面对公权力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基本的纠错能力,这是难辞其咎的。警察刑讯逼供,检察院滥用国家公诉权,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存在的,但如果法院能够坚持原则、保持底线的话,照样可以防止冤假错案,这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现在已经几乎完全失守。
记者:中国刑诉法1996年就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强调“禁止刑讯逼供”,而且正因为诸多冤假错案发生,比如河南赵作海案,在中央政法委主持下,最高法院以及最高检、公安部等联合发布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规定。按理这些年法院“敢于说不”的依仗应该是越来越多吧?
陈瑞华:用“非法证据”排除的方式来治理冤假错案,在实践中其实效果是相当差的。我举个例子,2012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曾组织在北京某法院观摩刑事案件开庭,庭审中公诉方出示八份口供,当庭排除了两份,获得现场旁听的一片喝彩。但问题是,还有六份呢?实践中,只要有一份口供就可以定罪。所以指望非法证据排除来解决冤假错案能走多远?我一直觉得,利用非法证据排除来制止刑讯逼供,继而解决冤假错案问题,其实很悲壮,像堂吉诃德和风车的作战。各国法制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非法证据排除来解决刑讯逼供,因为成功率很低。在美国那样的国家,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成功率也是连10%都不到。
记者:那你觉得要怎样才能解决问题呢?
陈瑞华:要从源头上找治理的方式,就像大禹治水,不是等着出了问题被动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台一些应景的规定,除了平息民愤、公众舆论,实践中几乎没什么作用。
在具体案件中,法院之所以不敢坚持法律和事实宣判当事人无罪,核心原因在于:第一,不独立;第二,无权威;第三,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倾向于追究犯罪,放弃了公正审判的基本能力。
先说独立性问题。当前大陆的司法改革,也想解决法院的独立审判问题,保证法院依法独立使用审判权,这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点。这一点从中央到地方到社会各界都有共识了。但实践中能不能真正做到呢?很多重大案件,尤其是命案,一旦发生必然引起党委、政府的重视,舆论也高度关注。法院很容易迁就当地的党委、政府,迁就当地的民众、公共舆论,以及被害人家属情绪。所以即便发现是冤假错案,肯定也不敢宣告无罪,因为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
其次是权威性。面对公安,面对检察院,大陆的法院一点权威都没有。强大的公安机关,政治地位比较高。现在地方上很多公安局局长不一定是政法委书记,但肯定是政法委副书记,地位照样高;检察机关地位也高啊,宪法上是法律监督机关,他可以监督法院,甚至同级检察院可以对同级法院立案,追究责任的。在极个别地方发生过,法院宣告无罪,检察院便直接抓法官。这种体制下,法院宣告无罪,要得罪公安、得罪检察院,它敢吗?面对可能的冤假错案,哪有纠正的勇气。
最后,完全倾向于打击犯罪。实践中,大陆的很多刑事法官,有时比检察官追诉犯罪的倾向性还强,一点公正性也没有。这是因为多年实践传统,法院已经变成打击犯罪的第三道工序,法官是打击犯罪接力棒的第三棒,第一棒公安,第二棒检察官。
记者:这些问题过去也说过很多次,但改变起来很难?
陈瑞华:一方面要从制度上去改变。比如中国刑诉制度中,法官审案开庭前就全部阅卷,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立案、侦查、起诉的材料全都交给法院后,一个法官,把这些案卷看完,会先入为主,“被告人是有罪的”。导致后面的法庭审判完全流于形式,什么法庭调查、辩论都没用的,而且中国的刑事审判是有审限的,法官办案时间又很短,除非特别大、复杂的案件,大多就开庭半天审完。请问半天时间里,能给律师充分辩护的时间吗?完全通过阅卷产生的内心预断,证人不出庭,鉴定人不出庭,法庭审判必然出现一边倒——控方强大无比,受不到任何有效的挑战;辩方极为弱小,引不起法官的注意,整个法庭审判流于形式。
很多冤假错案的例子还说明,即便是先入为主的阅卷和流于形式的审判,也能发现问题,证据不足,有可能无罪。但法院的考核体制使得法官要判一个无罪,比登天还难。如果法官判无罪,首先要汇报给庭长、分管的院长,要报告审判委员会开会,全法院里面看这个法官的眼神都是怀疑的,“是不是进行权钱交易了?”公安、检察机关不同意,法官还得去跟他们解释,还得跟政法委汇报去。反过来,判有罪有多容易?法官一个人就说了算,没人管他。可以这么说:一个法官判有罪,是一马平川,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职业风险;一个法官要去判无罪,会经历体制上的多重困难。从人性的角度,你说他本能地会宣告有罪还是无罪?
还有一个问题是功利主义的风险转移。很多冤案都能看出,上级法院不敢承担责任,把大量的风险转移给下级法院,明知道案件有问题,上级法院不直接宣判无罪,退回给下级法院重审,但下级法院很多时候是没法承担风险的,面临政法委的压力,面临公安、检察院的压力,面临被害人的上访,最后就出现了一个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留有余地的判决”,基本规律是上级法院不敢坚持独立审判的精神,把风险转移给下级法院。一方面希望下级法院不要动辄宣告有罪、判处重刑;另一方面,也不希望下级法院直接宣告无罪。然后就出现了最奇特的一种法律现象,明明证据不足,可以宣告无罪,却对被告人定罪,但又量刑从轻,留有余地。我过去写过文章指出,很多中国冤假错案的发生根源都在这儿。核心问题是中国的法院不敢坚持独立审判精神。
以上这些,都要从制度上去解决。
但另一方面,也要从法官自身找原因去改变。我是国家法官学院的兼职教授,我给法官们讲课时,经常举一个例子,当年某一冤假错案发生后,舆论压力极大,当年办这个案件的所有人员都被调查甚至“双规”,后来其中一个当年的办案人员就跑到一个墓地上,咬破手指用血写了“我冤枉”,然后自杀了。我在讲课中提出,维护司法公正、纠正冤假错案,跟每个法官的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不能做到,你自身难保!”我讲到这里时,全场鸦雀无声,法官们不再交头接耳议论,听得十分认真。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也提出倒查问责制、责任终身制。这对司法官员影响很大,影响他们今后的前途命运。
公安、检察院的公权力必须有所约束
记者:你刚才说过,中国刑事司法是一个流水作业式操作。如果追究源头,防止冤假错案恐怕不能只指望法院这最后一道防线,应该往上寻找原因?
陈瑞华:我个人觉得,检察机关造成冤假错案发生的原因,现在总的研究不够,缺少认真反思的精神。在中国大陆,根据《宪法》,检察机关不仅是公诉机关,还是一个法律监督机关,可以监督公安机关、法院、监狱,等等,防止他们违法办案。
正是这种检察机关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强势的地位,导致法院很多时候不敢宣告无罪,这是一些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检察机关可以对同级法院法官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这不就是让所有法官生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之中吗?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你如果没事,你怕他干吗?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体制下,谁不怕查呢?而且抓的不一定是宣判无罪的法官,法院里随便抓一个法官,整个法院工作都会受到冲击,产生负面影响,法院院长出于受到的压力就会阻止无罪判决。
我曾在最高检察院的会议上,毫不隐讳地说过,检察机关强大的监督权,可以对同级法院立案侦查,是中国冤假错案难以禁止的重要原因。我认为,应该禁止同级检察机关对同级法院立案,以后对法官的立案,一律交给省一级检察院甚至是最高检察院。
除了检察院的法律地位外,中国法律给公诉方的权力也过大,造成控辩双方严重不平等。
比如法律明文规定,一审判决出来后,检察院一旦抗诉,二审必须开庭;但如果被告人不服上诉的话,并不必须开庭,连开庭都不开庭,还纠正什么冤假错案?如果一个生效判决,检察院认为有错,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这是启动再审的法定理由;但被告人及其律师的申诉要想提起再审,非常难。申诉和抗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此外,中国检察机关拥有批捕权和公诉权,这两个权力合二为一导致检察院侦办的案件只要一批捕,就是定罪的前奏,量刑的预演。批捕这个权力在西方国家,几乎都是交给法院的。因为批准逮捕权很严重,一旦逮捕,就会让人感觉这个人是有罪的。这个权力不能交给警方和检察院的。捕诉合一的体制,权力高度集中,逮捕错了,公诉就要错了,一错到底。有些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机关是始作俑者。当初捕错,为了证明自己捕对了,必须公诉出去,并给法院施加强大压力。这么多年来,法学界一直在呼吁,把批捕权交给法院,但一直没有实现。
我举这几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大陆强大的检察机关拥有强大的公诉权,法律赋予其在追究犯罪角度上无穷无尽的资源,带有垄断似的很多诉讼权力,给被告人、辩护人的权利却极其弱小。一旦发生了冤假错案,推动程序纠正起来非常困难。
记者:说完检察院,下一步应该是公安机关了吧?
陈瑞华:公安机关承担着90%以上的刑事案件侦查,是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第一道关,但体制决定了其侦查权几乎不受限制,甚至可以说在有些情况下是肆无忌惮行使侦查权,中国大陆的公安机关权力之大,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尽管这几年有一些改革变化,但变化还是太慢。
公安机关的侦查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几乎到了不受任何有效约束的地步。我们知道,冤假错案发生往往和刑讯逼供有关,刑讯逼供往往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方式有关。但在目前的体制下:
—讯问嫌疑人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实践中经常出现半夜或凌晨开始讯问嫌疑人;讯问嫌疑人的时间持续也没有限制,实践中经常出现几天几夜连续审讯,超过人体的生理极限。目前刑诉法只规定了拘传不得超过24小时,但被拘留或逮捕羁押后,审讯时间就无限制。
—讯问没有律师在场,同步录音录像是公安自己操控,实践中几乎不受控制。
—犯罪嫌疑人一旦作出有罪供述,就彻底没有机会翻盘。在实践中,只要犯罪嫌疑人有过一次认罪供述,哪怕后面无数次翻供不承认,这一次供述就会作为呈堂证供。很多冤假错案都是这样,侦查时供述过,但开庭当庭翻供,比如云南杜培武案最典型,他甚至当庭拿出血衣证明自己是在受到酷刑情况下供述的,但法院根本没有理睬。
这些都说明中国刑事司法的“口供中心主义”,只要在公安侦查员那里有过认罪笔录,就可以永远作为定罪证据。
其次是辨认程序问题。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案等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除了刑讯逼供以外,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辨认程序存在重大问题。辨认犯罪现场或者辨认被害人尸体,公安机关组织的辨认过程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辨认环节没有律师或独立第三方参与,很容易出错,也是公安机关造假的最好时机。很多法治国家都规定辨认过程必须有律师到场,否则无效。但中国的辨认过程是高度封闭的,是完全被侦查人员控制的。
第三,鉴定过程存在问题。中国古代还强调命案要当堂开棺验尸,各方人等在场。现在大陆刑事案件的鉴定程序却完全是封闭的,公安部门的人侦查、鉴定一条龙,即便外聘也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缺乏监督。鉴定过程没有利益相关方到场,也没有律师监督见证。
上述这样的制度下,除非公安人员都是天使,否则无法避免案件出问题。侦查制度的封闭给极个别心怀不轨人员或者不负责任的人员制造冤假错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悲剧一次一次发生,但教训丝毫没有吸取。中国刑诉法修改中,有学者提出,讯问、鉴定、辨认都应该有律师到场,立法部门当即给否决了,因为公安机关反对,检察机关反对。
除了上面说的案件侦查中的问题,公安机关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传统,在案件还没开庭,没有定论的时候,先入为主制造既定事实,给后面的审查起诉和判决制造强大压力。这具体表现为:
—案件侦查结束以后,刚刚移交,法院生效判决还没有做出,侦查机关就可以搞立功嘉奖大会,对所谓“破案有功”的人员进行表彰,一方面将犯罪嫌疑人妖魔化,一方面向全社会先入为主传播所谓犯罪事实。各种媒体报道,党政人员出席大会。这会对后面的司法程序造成影响和压力,这个在法律上又很难纠正,是实践中的惯例和做法。
—涉案财产预先处置问题。浙江吴英案就是典型,案件还在侦查当中,法院生效判决还没有做出,居然就已经将涉案财产拍卖处理掉了。法院如果判无罪,最后怎么向当事人交代?这不是和整个政法体制作对吗?这里面有利益问题存在。
—还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命案,比如死者是公务员或者官员,案件还在侦查阶段,死者就被列为“革命烈士”。这是一种强烈的暗示,杀害“革命烈士”,那被告人还不得被严惩吗?
—侦查机关先入为主定性,制造既定事实还包括案件告破可以发新闻通稿,制造舆论影响。现在很多地方要求律师办案过程中,不得在媒体上随便把辩护意见发出来,否则要受批评说违反职业伦理,甚至要惩罚处理。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自己侦破的案件发新闻通稿却丝毫不受限制。比如福建念斌案,最后宣告无罪,但回头去看当年公安机关所做的宣传,看看那个报道,把念斌彻头彻尾妖魔化了。这种做法,不但给法院制造压力,也给被害人形成强烈刺激,让他们坚信被告人是凶手,给纠正冤假错案制造更大的障碍。
所以我经常说,中国的侦查机关,权力不受节制,权力行使没有纳入法治轨道,在实践中就会变成洪水猛兽,成为脱缰的野马,不受法治的控制。
现在是治理冤假错案的最好时机
记者:你刚才也提到了刑事案件中辩方力量弱小,那如何提高呢?律师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得到发挥?
陈瑞华:从根本上说,律师作用得不到体现,是被告人地位低下的体现。毕竟律师的权力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委托,所以核心是要提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
当然,律师不完全等同于当事人,有其职业特点,目前在纠正冤假错案的制度设计上,律师的作用确实没有得到重视,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官方相关文件在关于律师发挥作用的问题上都是一笔带过。
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律师是法律职业人群体里最活跃的,无论是接受当事人委托,还是根据法院指定进行法律援助,都能对案件起到很好的纠偏作用。西方有个说法,“律师的辩护是法官最好的助手”,律师权最善于发现案件的疑点、漏洞、矛盾,可以对侦查机关过大的侦查权形成制衡。
目前大陆的司法还是所谓“政法干警”概念,公检法一体化,律师排除在外,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很难形成。最近有一些变化,比如最高法院在死刑案件复核中,强调听取律师意见,这是可喜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太慢。
记者:防止冤假错案与打击犯罪有时候是很难两全的,尤其中国的老百姓传统而言更追求安定,过分强调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会不会导致民意难以接受?
陈瑞华:你说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存在,尤其现在中国的主流舆论是反腐,要将贪官绳之以法,老百姓有一种打击犯罪的渴望,公安及时破案也是得民心的。这种情况下法院发现证据不足、证据有瑕疵就宣判无罪,肯定会惹怒整个社会,且不说来自被害人家庭的抗议,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就让司法机关难以承受。
所以必须权衡两种利益,犯罪不能处理的危害与冤假错案对社会带来的破坏,哪个影响更大?
打击犯罪,全社会都有预期,符合所有人利益。但近年来,对公权力怀疑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的,民众对公权力不再盲从,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民众的权利意识在提高,目前人们对公权力滥用的警惕已经超过对犯罪不能处理的敏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惩治腐败”,这些归根结底都是政治话语,公权力滥用才是最可怕的,才应该成为人民公敌,这个舆论场已经形成。有了这个舆论环境,我个人觉得,中国治理冤假错案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机。
可以说,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让我对未来还能感到乐观的地方。当然,具体到个案中,也需要一些技术化改革。大陆的法官不容易,在目前体制下,将心比心,要把证据不足的案件宣判无罪,很难做到。所以学界也建议大陆逐步推进陪审制度,法官不必事必躬亲,还可以在具体个案中分解压力。
不过陪审制的改革需要时机,从人类陪审制改革的历史来看,与政治改革是密不可分的。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
图集